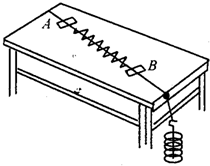说到杨立青任院长期间的行事风格,钱仁平回忆说,“他平时人特别好,对每个人都很和善。但是一旦他决定的事情,就会雷厉风行地执行。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大家都特别相信他、打心底里服他。”——题记
杨立青访谈录
访谈者:钱仁平
时间:2012年9月8日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研究与发展中心
钱仁平:杨老师,您是全国很著名的唱片发烧友、“唱片大户”,今天的访谈我们就从唱片说起吧,为什么买那么多唱片?
杨立青:买唱片算是养成的习惯吧,或者说是家传。首先跟我父亲有关。可以想象在五六十年代,音乐会很少,接触音乐的媒介、接触一流演奏家的机会可能只有唱片了。我父亲那时候有点“过分”哦。他有个学生,是国立音专的,刚解放的时候到巴黎音乐学院留学,50年代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当老师,带回了一批唱片,一百块左右一张。他就把所有的储蓄拿去买唱片了,至少花了两三万块钱,真是不可思议。(笑)
钱:这些唱片对于您的音乐生活,比如创作、教学应该是有很多的好处吧?
杨:当然了。接触到的很多新东西都是从唱片开始的,比如说第一次听巴托克,我还记得是1962或1963年在王建中先生家里。王先生也是喜欢唱片,我跟他学和声。当时我不到20岁,印象特别深刻,他跟我讲,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是库塞维斯基(Sergei Koussevitzky)指挥的:库塞维斯基认为《乐队协奏曲》是20世纪最好的管弦乐作品。
钱:现在您家里有多少张唱片了?
杨:总有1万多吧。

钱:下面我们聊聊最近创作的《木卡姆印象》。这部作品2012年6月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新疆十二木卡姆交响音乐会),后来好像又复演了一次。
杨:对,没错。8月底又在北京演了一次。据说效果要好得多。
钱:这个作品起因我知道一点。有一年您去新疆采风,好像是文化部组织的是吗?
杨:是。文化部这个项目的缘起据说跟赛福鼎有关。赛福鼎曾在国外听了交响乐之后,就想把新疆的“木卡姆”变成交响音乐。他去世后,家人就向相关部门提出了赛福鼎的这个愿望。所以,文化部就组织了一批作曲家去新疆走走看看。
钱:怎么想到是大提琴与管弦乐队,可以直接叫作“大提琴协奏曲”吗?
杨:我就把它叫做“大提琴协奏曲”。用大提琴第一个原因可以这么说吧:当时在听了一些“木卡姆”后脑子里就在想,“木卡姆”这么一种很丰富的东西,那么浓郁的特色,如果完全按照它原本的结构、音调去写会碰到很多问题,它毕竟是歌舞音乐嘛。“木卡姆”里有很多微分音没法处理,交响乐队怎么进入中立音呢?当然你用很“先锋派”的方式去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想着用一件独奏乐器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
钱:是不是说“木卡姆”的因素主要通过独奏乐器来体现?
杨:不。只是独奏乐器可能会比较灵活一点。第二个原因是我听了他们收集的“十二木卡姆”录音,从中选了一点素材。这个素材是一个吟唱,后面伴有新疆弹拨乐器,像空弦那样的音,这跟大提琴的音区比较像。如果用大提琴来表现它那个吟唱的风格,就像游吟诗人那样的感觉,然后和五度拨弦结合在一起,所以最后就决定用大提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写了不少东西都是独奏乐器与乐队的,协奏曲类型,二胡和乐队、琵琶和乐队,诸如此类。为什么我常常使用这样的结合?这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停顿了一下)我对我们的乐团不大放心。我们乐团都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团里的每个演奏员的技术都不错,但不练琴。要演出的作品在家里是不练的,到了排练的时候就视奏,但又没多余时间给你视奏就直接进入演出排练。于是,每次你听到的东西都是“夹生饭”。
钱:那《木卡姆印象》首演您满意吗?
杨:当时我觉得还不够。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在配器课上我也跟学生说,我们的乐团现状或者说是演奏习惯,作为作曲家我们常常不知道“是我写的不好,还是他奏的不好”?!
钱:对!对!对!
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能奏出来的,但往往一塌糊涂、乱成一片。那么是我写的不好吗?我有几次经验证明并不是这样。比如《乌江恨》,它的首演是在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不算特别好的乐团。但是拿回来的录音,我们的“上交”或者国内其他乐团都没有达到过。不是速度上不去,就是铜管又冒“泡”了。还有《荒漠暮色》,香港首演之后也由日本的一个交响乐团演,演出前他们共排练两次。我去听了,基本上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后来,这个作品由“国交”、“上交”、“上音”的乐队也都演过,没有一次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我们乐团演奏员的个人水平肯定比日本的高。但人家事先都在下面练好了,加上乐团以及指挥对现代音乐也比较有经验,所以很容易把新作品的基本面貌弄出来。
讲个我的老师王建中先生的故事。大概是在80年代末,一次我见他在学门口走来走去,便问他在干嘛?他说,里面在排练他自己的作品。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听?他回答说,不敢听。“不敢听”就是说他很担心会奏得一塌糊涂。作曲家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无能,写成了这个样子。这个问题常常让我很纠结,写得很简单我不甘心,但是你给乐队负担太重的话他演奏会出问题。然而,你找一个比较好的独奏家,他能把整个作品的基本意图体现出来。乐队作为协奏曲来讲相对容易处理一点。这样可能好一点。
钱:那么《木卡姆印象》的乐队部分是充分考量了演奏因素的。您刚刚也提到,您的这种协奏曲类型的作品很多,那这部作品与以前相比,独奏乐器与乐队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杨:这回更多地是从协奏曲来考虑。《霸王卸甲》、《乌江十艮》原来都不把它们叫做协奏曲。在日本演出的节目单上是用英文写的,叫做“Symphonic Ballade with Pipa Obligato”,为交响乐队与附加的琵琶而作的交响叙事曲。
钱:这些作品在您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木卡姆印象》、《乌江恨》、《霸王卸甲》还有《一枝花》我觉得是有点一脉相承的。
杨:说它们相似,(首先)都是委约作品。委约作品都带有审美的前提。《乌江恨》是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和念书时候教我配器的施咏康先生有关。回国后他对我说:“杨立青,你回来以后别再写国外那种风格的作品了,写传统一点的,让大家认识你、知道你。”他认为,要让大家认识、了解你,得要用扎实的传统功底,用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去写作。二是当年南京的石中光老师被邀请去指挥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日方提出希望有一首中国乐器和交响乐队合作的作品。石老师就跟我说,他们正好有一个琵琶演奏员擅长演奏《霸王卸甲》,能不能就把《霸王卸甲》跟乐队弄在一块。当时我就答应了,但又不大甘心就配个伴奏,于是写了三十分钟。《霸王卸甲》是一个古曲,要写得非常现代,我当时还没找到那个途径。后来我发现周龙的《霸王卸甲》写得很好,用了很现代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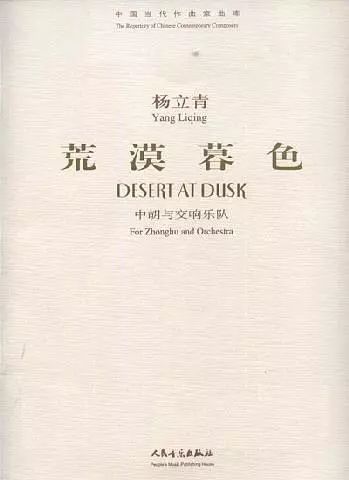
钱:是不是说创作时民族素材比较完整保留,但是在管弦乐部分花了很多心思。您说了作品不是很现代。
杨:我指的是在音乐语言上。梁茂春老师有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准确,他谈《乌江恨》,说“在传统与革新之间”。《江河水》、《一枝花》也带有一点委约的性质。1991年,李黎夫希望把中国一些传统名曲改编成交响乐队推到国际上去。同时,中国唱片厂上海分社的一个编辑找我,说准备出一张CD,曲目除《梁祝》外希望再有一首某件民族乐器的协奏曲。这两个机缘结合在一起,我就决定用二胡与乐队写《江河水》。而且《江河水》本身就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传统曲子。后来,陈佐湟把《江河水》带到“国交”去演出。1997年作品被列入了“国交”成立后首次欧洲巡演的曲目。他后来还提出能不能再写一首更欢快一点的,于是我就创作了《一枝花》。因为作品是拿到国外演出,如果做作品标题直译“flower”,外国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根据曲子的结构——前面有个引子,接着是上板,最后是快板,改了标题叫《引子、吟腔与快板》。这两部作品都为“国交”写的,“国交”那时水平很高。
钱:《荒漠暮色》是在“天津会议”上放的。当时大家都认为是很难得的一部中胡与大型管弦乐队作品。但它的创作手法与刚才我们说的作品不一样,这个作品又是一个怎样的创作背景?
杨:《荒漠暮色》也是委约作品,为了在日本举行的一场纪念丝绸之路的音乐会。写作的时候准备工作是比较重要的。我用一个音高模式做了若干和弦,这些和弦构成作品和声大体的样子,在这首曲子里是很自由的,不是严格的序列。这个作品接近音色音乐,骨架声部是有音列的,但音列的处理是很自由的,不受它的拘束。结构上开始是散板,逐渐形成节奏律动,然后是那种类似很宽广的东西。这是与我脑子里想象的一个广阔大漠联系在一起的。我后来后悔了,不应该叫“荒漠暮色”,应该叫“大漠暮色”。

留学生涯
钱: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作曲家,您是哪年出国又是哪年回来的呢?
杨:我考取留学(资格)是1978年,1979年开始学语言。1980年初去德国到1983年4月份回国,一共三年多。
钱:您在德国的学习和游历对您的创作影响大吗?
杨:那当然很大了。《磬》(CHIME)上面有篇文章,开玩笑地写我在刚出国时对现代音乐一无所知。
钱:这句评价您觉得合适嘛?您不是买了那么多的唱片。
杨:当时虽然买了很多唱片,但“最现代”只听到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认为《春之祭》是非常新鲜的东西了。弹过兴德米特一些的钢琴曲。勋伯格接触过一点,摸过几首曲子,但对十二音技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了解。巴托克接触相对较多一些。在那时,我脑子里的现代音乐也就是这些了。
初到德国以后有几件事印象深刻。我到汉诺威音乐学院图书馆去借唱片,才第一次见到潘德列斯基的名字。听完他的大提琴协奏曲后我全懵了,全是噪音没有主题,我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所以,我才说我对现代音乐一无所知。
另一件事,我到了汉诺威音乐学院后才知道拉亨曼就在这里当教授,我上过他的《20世纪音乐作品分析》课程。最有意思的是,出国前我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内部油印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上第一次看到拉亨曼的名字,是一个音乐学家写的谈70年代联邦德国音乐。文章里引用了拉亨曼的一句话很有意思,“现在人们又可以在音乐的床上尿床了”。我当时就想说讲这么刻薄的话是谁啊?搞了半天就是我们学校的教授。
我刚到德国的半年很不习惯这样的音乐,于是给邓尔敬先生写了一封信。邓先生回信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让你去,你就好好地钻进去再跳出来。”当时在国内,我自认为是不算保守的。但是潘德列斯基、里盖蒂他们作品里是没有主题的,也没有习惯了的节奏。于是我就觉得有些慌了。
当时邓先生那番话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好吧,那就先进入虎穴吧!”真钻进去了解了作曲家为什么这样写之后,就觉得非常有意思,觉得这些作品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思考的。所以回国后我在一次全国交响乐创作座谈会上讲过一句话“要补课”,也写过一篇文章《由“补课”说开去》。德国在纳粹统治时代,所有的现代音乐是禁止的。“二战”后,德国人在文化的废墟上思考应该走一条什么路来建设现代音乐。他们称之为“补课时期”,就是“达姆斯塔特暑期营”,从那时开始德国作曲家有了新的变化。
达尔豪斯曾在一套德国的唱片资料上写到“60年代中期,当约翰·凯奇的音响到达欧洲的时候,有一些天才的作曲家退出了舞台”,里面举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的老师科尔本。他是当时德国音乐协会主席雅格比访华时给我选的。

钱: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杰出的作曲家不一定是一个杰出的作曲教授。比如肖斯塔科维奇的老师斯泰恩伯格,就作品而言现在谁会知道呢?但是这位老师能在全苏联都在批斗肖氏的情况下,站出来力挺他的学生,这一点还是很感人的。
杨:我的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对中国学生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吃不准。我一去,他让我做一道很难的和声分析题。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的“和声”不用上了,你们中国用的什么体系啊?”我说,“曾经学过斯波索宾,苏联的。我们的老院长丁善德先生曾经到过法国,桑桐先生研究过德国音乐理论家里曼的东西。”他说,“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怎么你都会?”他认为我的水平很好。我自己觉得复调是一个薄弱环节,后来就去攻复调。他们的复调也从严格对位开始,但不光是一对一、一对二这类,实际上是让你写宗教音乐。拉丁文的歌词,让你写合唱,用类似于圣咏的方式来写。但是这种东西我写不好,一个是文字上的障碍,还有一个音乐语言风格接触得少。但是写到巴赫时代四声部赋格的时候,我的老师很惊讶,“你们中国有多少人能写成这个样子?”我说,“我们作曲本科毕业都可以。”他不相信,说德国人没几个能写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我要拿学位需要去大使馆延长签证时间,老师给我写鉴定说,我到德国之后钢琴演奏技术突飞猛进,在学校里面非常受欢迎,有很多人的作品演出都让我去弹。同时,对当代音乐语言的了解越来越多,是他见过的亚洲学生当中最好的一个。当时我还心里不高兴,怎么只是亚洲学生里最好的,为什么不拿我跟欧洲学生比比。(笑)当然这是开玩笑说的啦。
《洛卡尔诗三首》那是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写的,相邻的两个和弦之间对斜的同音都不可以,更不要说同时出现的和音了。这个作品当时我的老师是很满意的,又不是像勋伯格那么典型的风格,可听性比勋伯格强吧。《唐诗四首》里面是使用了不同的方式,四首在风格上多多少少是有所不同的。第一首是两个调为中心;第二首听起来有点中国说唱的意思,但实际上是人工调式;第三首是minimal单音音乐,就是说所有的素材来自一个东西,有点支声复调;第四首是用固定节奏的声部和没有节奏的声部对置,在音色上的处理比较讲究。写的大型室内乐《为十个人的音乐》里面其中一个主题是类似于赋格段的主题,有点新古典主义,陈铭志先生在他文章里提到过。那时候没人写赋格。这个赋格段比较好玩,它是十二音,但不是序列,主题本身是混合节奏。十个声部一个个声部进来的时候夹杂着混合节奏,难度很大,所以后来我不用这一类手法了。但是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点子很有意思,用紧张度来控制它整个的和声语言,有点类似比兴德米特再走远一点的哈特曼。老师看到谱子说,“杨立青,你让我很惊讶,你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哪个巴伐利亚的德国人写的我也相信。”算是比较地道吧。
还有一个作品是管弦乐《意》。
钱:是你赠送给图书馆那个手稿吧?
杨:是。那个纯属是用音色音乐的方式来写的。写这个作品,老师要求我先画一幅抽象画,用点、线、面各种方式构成一个画面,然后把我所想象的线条和块状变成音高。这样你就可以感受到潘德列斯基的影响。
这几部作品可以说把新古典主义兴德米特的方式,梅西安的人工调式的方式严格的十二音序列方式,音色音乐的方式等等都尝试了一下。
钱:这是你有意识地想把当时那些“时髦”技法都实验一下。
杨:对。我刚去时对这些并不了解,但通过一些关于20世纪音乐的课程,你可以知道作曲家为什么这样写。
钱:那是大课?
杨:对。
钱:哪个教师教的呢?
杨:一位很意思的,也跟我关系很好的库珀科维奇教授。他是斯托克豪森的好朋友,斯托克豪森有几个作品是他指挥的。有次他分析斯托克豪森的《Mixtur》,叫班上每个人担任总谱里的某一个角色来进行敲打。这首作品的唱片就是他指挥的。我回国以后,还写信给他希望他把那张唱片翻录给我,总谱复印一份。后来,他干脆把斯托克豪森题了词的那张唱片送给我。他当时是汉诺威音乐学院院长,学院里有三个作曲教授:一个是拉亨曼,是极端先锋派;一个是我老师,是中间派:第三个就是这个他。他早期是极端先锋派,但到我在那里读书时已经“回归”了。德国的报纸评论他是“从先锋派到乖孩子”。他认为无调性音乐的发展是历史错误,所以他把自己写的无调性作品全毁掉了。
钱:他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蛮有意思的。
杨:他厌恶了,对现代音乐厌恶了。但是他课上的有些观点我印象很深。有次他放斯托克豪森的《MikrophonieI》,一个小提琴专业的学生说“为什么作曲家要写出这么难听的音乐?浪漫派音乐那么美,为什么不写那样的音乐?”尽管库珀科维奇自己已经“回归”了,但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浪漫派美化了这个世界”。这句话我后来常引用。当代作曲家真实地表现这个世界以及它在我心目中的样子,不光光是那些美好的旋律才是音乐,我们处在一个噪音环境当中,作曲家会需要表现客观环境对自己的触动。他上课讲很多这类东西,让我开始对现代音乐逐步地了解。通过这些课程和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在构思音乐的角度上拓展出很多不同的途径和思维方式,导致写出的作品有很多不同面貌。后来回过头来我非常感谢邓尔敬先生的话,进入以后你才知道这个世界。虽然里面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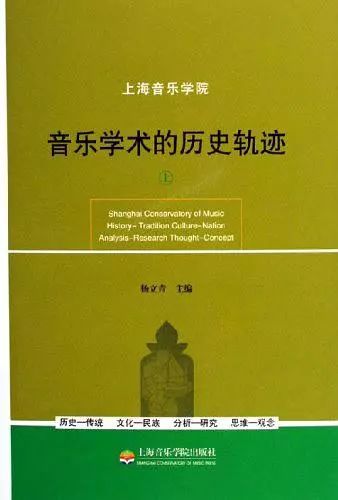
钱:留学前写过的作品中,您印象比较深是什么?
杨:很多啊,比如《山西民歌九首》,20岁前后创作的。
钱:那时在念附中?
杨:没有。休学养病,手坏了,后来肺又不太好。也就是利用了这个时间,跟王建中先生学和声。那时候喜欢在钢琴上弹点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德彪西的东西,自己也做一些创作。年轻时有创作冲动,进了大学后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1965年进大学,第二年就“文革”了。当然那中间也创作了很多,有一个钢琴与民族管弦乐队的协奏曲,叫《出海》。还有一些小舞剧,像《节日之夜》啦,还有钢琴伴唱《杜鹃山》。
钱:讲到舞剧我们还是要聊一下《无字碑》,这个作品是80年代吧?
杨:对,山东歌剧舞剧院委约的。当时他们很急,我怕来不及写就找了陆培。第一幕让陆培先弄起来,后来我们一人写了两幕。当时陆培跟我说想用一个谢德林的序列来写,我同意了。那就是我俩写作的共同素材。
钱:那个音乐今天来看仍然是中国舞剧中最先锋的。您的高足张千一也写了很多舞剧音乐,但是他一般是“不突破”的。前年在北京开“百年经典选曲”的专家论证会,我还说这部舞剧音乐应该选进去。另外电影《红樱桃》的配乐也是很有趣的。
杨:电影中音乐用得很少,如果把整个音乐单独拿出来听还是很好玩儿的。这部电影比较有戏剧性、交响化。可能我比较适合写这一类东西,悲剧性较强一些的,快乐点的我恐怕写不太好。
90年代的时候,香港雨果公司到大陆来找一些作曲家写New Age,带了一些唱片给我听。听完后我告诉他们,我不适合写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讲到New Age呢?我要说的是,我明白自己创作的局限性,或反过来讲也是我的特点。我喜欢写大起大落、充满对比的东西,悲剧性的东西,戏剧性能够得以展开的。而那种很平稳的、可以当背景音乐听的音乐,我创作不了。
钱:您写了这么多作品,回头看一看比较满意的是什么?留有遗憾的又是什么呢?
杨:我是一个自我感觉很糟糕的人,从来都不满意,总觉得好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更好的作品还在后面。当然话说回来,相对来说自己认为完整一点的、受到羁绊束缚少一点的还是《荒漠暮色》吧,更加是“我自己”一些。其他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会被一些因素牵制。我曾在《现代乐风》上说:“要找到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是作曲家一直在寻找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没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最近感觉好像稍微比原来顺了一点。从2000年我做院长开始,就基本上没法考虑创作了,有十年的时间只能写点文章。因为我创作的习惯和其他作曲家不一样,今天写8小节明天写20小节后天再写多少然后再开会去,这样创作我是做不了的,我希望集中一段时间什么事都不做,就只浸在自己的音乐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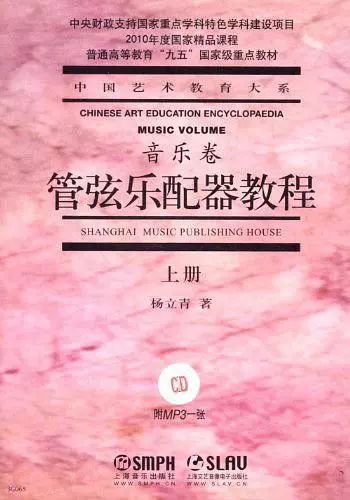
关于作曲教学
钱:要祝贺杨老师的配器书终于出版了,全国音乐界翘首以盼。其实您很早就在积累,当初我读书的时候都是那9大本讲义,还需要您签字再到教材科买。大家都知道在配器教学上您是花了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件事请您谈谈吧。
杨:我一直把配器当做一样很神秘的东西。我喜欢交响音乐,喜欢乐队色彩。我现在还留着6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辟斯顿的《配器法》。我到书店买回来后在上面提了一句话“连和声对位都没有学过的杨立青,购于62年几月几号。”我在课上一直给学生讲“最好的老师是实践”。我在沈阳音乐学院时,李劫夫写的大合唱都是不配器的,让青年教师或者是学生帮他做配器。“文革”时还“扒”过样板戏。《沙家浜》我“扒”过两场,《红灯记》“扒”过一场。写完了以后就与磁带比较,发现差在哪里,再等总谱出来与总谱比较。当时还写舞剧音乐,李劫夫写的诗词大合唱我们做完配器以后就现场听。有了这样一些实践经历吧,就觉得配器是很好玩儿的。后来毕业留校,就让我教配器,第一件事情让我编乐器法。
钱:那个时候就开始编乐器法了?
杨:对。那是75、76年吧。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考研究生其实定的方向就是配器。当时丁善德先生教作曲,桑桐院长教和声。配器是施永康先生上课,但是他没有研究生导师资格,于是我就挂在桑院长名下。我上了一年半就到德国留学了。之后,施永康先生要调到星海音乐学院去,学校开的条件之一就是“杨立青回来才能走”。于是乎,我回来后接他的班继续教配器。
我不大喜欢照本宣科,总想做有创造性的事情。我希望学生接触到更宽广的面,有意识地扩大当代音乐的比例,尽量从作曲的角度去寻找合适的例子,通过配器课了解现代音乐。第一次教配器,是给刘滠、叶国辉他们上的。头几年的时候和后面的教学不太一样。那时候喜欢按照风格分类,“古典”、“浪漫”、“印象”、“现代”。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很费劲,因为讲“古典”得讲弦乐,讲“浪漫”还得讲弦乐,很多东西都在重复。头几年上课用的谱例与现在也是不一样的。那些讲义是从80年代末开始写的,到1994、1995年整个讲义的结构基本上呈现出来了。再用了五六年的功夫把现在的格局定下来了,主要就是花时间把它充实,真正定型是到2004、2005年。
钱:我听以前同事讲,他是在俄罗斯读研究生,他的配器就是作曲主课老师教,而国内九大音乐学院都是差不多的模式,分“四大件”老师和作曲老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杨:我觉得这是一个共通的问题。我所到过的国外几所音乐学院,他们确实没有专业教配器的老师。最近维也纳音乐大学新出了一本配器教材,那个作者倒是在大学里专门教学配器的。但是比如说在汉诺威,配器是没有单独的老师上课的,做了几回配器作业,我的作曲老师说不用专门学习配器了。我们现在的模式是苏联模式,“四大件”、“五大件”,实际上按欧洲模式就是作曲工作坊,不论是哪一门作曲技术理论,和声、对位、音乐分析、配器都应该是作曲家来教,他都不是专门的理论教师。理论教师其实也是存在的,但是他不教作曲。
钱:对。理论老师应该教表演专业的学生,音乐分析有助于他理解曲目去表演作品。现在的情况是,所谓的“四大件”或者说作曲技术理论课程还是努力地想为作曲教学提供帮助,但是在作曲方面并不是很满意。在这种教学体制下,导致特别是现在年轻的学者,只想怎么为作曲学生提供捷径,但并不能定不下心来,潜心研究。从而自身的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其实是下降了。再之,“作曲技术理论”这个名词在西方有吗?
杨:在西方就叫“音乐理论”。像我的老师也上和声,但是他只把“浪漫派”的和声原则总结给学生。对位也是他上课。配器他不是给所有的学生上,只给有需要的作曲学生上。
在萨尔斯堡,我做过客座教授,那里的作曲教授也就两三位。一个是波兰人,叫伯格斯拉夫·舍费尔,写过一本作曲技法的书,很厚。还有一个叫维平戈,奥地利人,配器都是他们自己上。他们也有专门搞理论的,一个很棒的德国教授好像叫海瑟夫,在萨斯堡音乐学院专门教律学与声学,他的课我觉得非常受启发。他自己写过一本书,我一直建议去翻译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把作曲技法从中古时期一直到现在,以提纲的方式,举几个例子,用几句话点出各个时期作曲技法的要领。
钱:我觉得音乐理论与创作、表演实践以及音乐理论自身的问题等等是必须深入思考并逐步去改进的。今天辛苦杨老师了,感谢您。

音乐编译组公众号往期推送: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